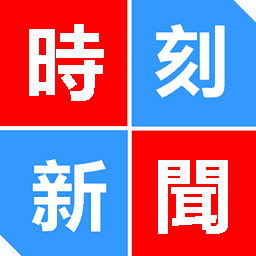2023年12月22日,北京清華大學铊投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生命令人悲哀地畫上了句號,而罪犯仍然逍遙法外。朱令案是那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中國權錢社會最殘酷的寫照 ,其實大多數的我們都是朱令。直到今天,司法公正在權錢面前仍然隻是壹紙空文。爲了紀念逝去的朱令,也爲了警醒健在的我們,本站特此全文轉發曾刊登於《博客天下》的這篇文章。
朱令走了,她到底還是沒有等到“那壹天”。
這是壹段被反復提及的青春,儘管當事者已經或即將進入人生的第50個年頭,但人們壹次又壹次把她們拉回到近叁十年前的那個現場——
4個清華女生,壹間宿舍,如詩的年紀,如夢的大學時光,如歌的同學友情……
如果不是壹起铊投毒案,這將是她們人生中最爲美好的回憶之壹,可殘酷的現實改變了壹切。
活着但已失去了曾經的姣好面容和聰明伶俐,取而代之的是大腦萎縮、基本語言能力喪失、雙目近乎失明以及100公斤體重的朱令,以及,這些年來則屢屢被強大的民間輿論所包圍她的叁位室友。
4人的青春鑲嵌在民意洶洶的時代裏,伴隨朱令案的每壹次發酵,不斷顯影。每壹個人都在竭力尋找真相,卻從未離真相更進壹步。
筆者曆時壹個月,近距離接觸朱令案中十幾位知情者,爲我們還原了多年前塵封時光中的交集悲欣。
(壹)
1992年9月的壹天晚上,29位清華大學物化2班新生席地而坐在校園內荷塘邊的草坪上,新生們開始自我介紹。
這很可能是孫維和朱令第壹次壹起參與集體活動,這是看不清人臉的壹夜。
來自北京的學生張利記得,老師讓每個人用家鄉話介紹自己從哪裏來。從內蒙古遷來北京多年的張利順口說了句“丫挺的”,孫維立刻說:“這是罵人的話!”
這是孫維第壹次在全班同學前亮相。
“孫維很耀眼。”這是張利對這位北京老鄉的最初印象——那天晚上張利沒有記住跟孫維同宿舍的另壹位北京老鄉朱令。
在自我介紹前,物化2班學生在清華校園內的主樓廣場舉行了開學典禮,當天的校報記載,他們聽壹位新同學代表全校師生做了壹場關於如何做好社會主義接班人的發言。
當天白天,這群92級新生剛剛完成了他們的開學報到。
鄭智化的《水手》和《星星點燈》在新生入學的過程中循環播放,併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聽這樣的流行歌曲,多年過去,張利仍用“哭腔”形容這兩首不斷滾動播放的歌。
這壹年的上半年,***剛剛完成了對南方的視察,而更早壹年,壹群從大學出來的知識分子下海經商:
失意者俞敏洪離開北大英語係,醞釀創辦“新東方”;馮侖和合作者則分頭借錢,籌得3萬塊,成立了海南農業高技術聯合開發投資公司。待這批人取得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後,他們被統壹冠以“92派”這個稱呼。
在當年清華2143名報到的本科新生中,陝西寶雞的王琪、新疆昌吉的蒙古族女生金亞、北京的朱令和同樣來自北京的孫維,在繳納完5年的住宿費125塊錢併領到壹床新被褥後,終於來到了她們將要生活5年的寢室——清華6號樓的114寢室。
據去過寢室的朱令母親回憶,推開114的宿舍門,兩張雙層架子床靠着兩面牆。北京女孩孫維和朱令都選擇了上鋪,新疆的金亞住在孫維的下鋪,陝西的王琪則最終選擇住在朱令下鋪。
朱令在床鋪上支起了壹個小架子,經常參加文藝表演的她會在架子上擺放各種化妝品,例如壹支口紅。
這間寢室靠窗的位置擺放着壹張桌子,朱令有時會把她的水杯放在桌上;進門右手的長桌上擺放着寢室裏4位姐妹使用的洗澡籃;朱令的隱形眼鏡小盒則放在進門左手的公用架子的最上方。
這間寢室的4位女生併不知道她們將因這場匯聚而改變命運。
(二)
在未成爲室友之前,這4個女孩以各自的方式度過人生的花季。
朱令和孫維出生於1973年,王琪和金亞要稍小壹點兒,出生於1975年。
接受採訪時,朱令母親朱明新解釋:“北京小孩上學卡得比較嚴,不到7歲不讓上學。不像外地的孩子,可能早壹兩年就上學了。”
而這也成了朱令後來選擇上清華而非北大的原因之壹,因爲自己感覺年齡偏大,朱令很難接受1990年代初期北大長達壹年的學前軍訓。
與父輩相比,“文革”對她們的影響可能併不深刻。她們的童年恰好處於壹個國家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轉折時期,蒙冤者逐漸得到平反,人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受到重視,經濟復蘇,百廢俱興……
放眼四顧,到處都充滿了向上的力量和壹種從頭再來的豪情。這爲她們成爲那個時代的“好學生”鋪下了底色。
朱令在北京光明小學的同學王曉麗,如今是“幫助朱令”基金會的志願者之壹。她對小時候的朱令印象深刻:
特別聰明,自主學習能力很強,討老師喜歡。“老師對別的同學以批評教育爲主,但總是勸朱令多休息,多去玩。實際上,朱令學習不是特別用功,她效率高,該玩的時候就玩。”
王曉麗說,小學時的朱令還當過班幹部,但具體什麽職位不記得了”。在王曉麗的記憶裏,朱令數學成績尤爲突出,且“遊泳很好,還有證書”。
她還記得在壹次手工作品展上,朱令做了壹個日晷,“跟故宮裏的壹樣,可以根據太陽的光影變化來確定時間,這讓同學們都覺得朱令不壹般,她的想法比我們多”。
朱令的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匯文中學度過。朱令上大學時表現出來的多才多藝也許與這段就學經曆有關。
這是中國最早的壹所教會中學,始建於1871年,最初爲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設立教堂時附設的“蒙學館”,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爲市立第二十六中。在壹批匯文老校友的努力下1989年又重新恢復校名,併挂上了早期匯文的英文銘牌PEKING ACADEMY。
這是壹所帶有濃厚西方現代教育理念的中學,素有重視“全人教育”的傳統,校訓上寫着“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爲北京大學原校長蔡元培所題寫。
朱令的姐姐吳今(隨父姓)曾經也就讀於這所學校,併以當年崇文區理科第壹名的成績考入北大物理係。和朱令壹樣,吳今在音樂上頗具天賦,且喜歡跳芭蕾舞,曾是北京大學校舞蹈隊的主要成員。
網上壹篇名爲《朱令家庭小傳》的文章這樣描述姐妹倆:
“姐姐更漂亮壹點,妹妹身材高壹點,兩人各有千秋,都是人見人愛的女孩兒……至今我還記得當年到她們家玩,姐倆在壹架鋼琴上合奏的樣子。
當時演奏的曲子是小貓小狗圓舞曲,曲風诙諧幽默,那時他們壹家人充滿了歡笑,是令人神往的美滿家庭。”
這個家庭在1989年春天被命運打開了壹個缺口,正上大二的吳今在學校組織的壹次野外遊玩中,不幸墜崖身亡,那年朱令在讀初叁。
這件事給了朱令很大打擊。
壹位朱令的中學同學說:“我還記得當時朱令在食堂邊上的小花園裏面栽了壹棵樹紀念她姐姐,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了。”
在距離匯文中學不到10公裏的西城區西皇城根附近,是北京市的另壹所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所在地。就在朱令失去姐姐的幾個月後,孫維進入了這所學校的高中部。
詩人北島是這所學校的校友之壹,他曾在《北京四中》壹文中如此表達他時候對北京四中的憧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國最好的中學之壹,對我來說就像天堂那麽遙遠。”
這所學校之所以有名,還在於它在“文革”期間被稱作“紅牆子弟雲集之權貴學校”,很多高官子弟都曾在此就讀。
孫維同樣有着不錯的家庭背景。
父親孫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員,北京市地震局下屬的某公司第壹任法人代表;爺爺孫越崎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是中國能源工業創辦人和奠基人之壹;伯父孫孚淩(孫越崎侄子)曆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高中時期的孫維究竟是什麽樣子,由於缺乏確切的細節和描述,很難還原。壹位自稱是孫維鄰居的網友曾在天涯社區非常籠統地用3句話概括了他所知道的孫維:“從小學習不錯,北京四中畢業,考上清華大學。”
在這之前,還有壹位自稱是孫維高中同學的網友用“活潑開朗”來形容那時的她。
對孫維來講,3年的高中生活有重要意義,她不僅從這裏考上清華大學,還在這裏遇到了後來的丈夫謝飛宇,他們是同班同學。
(叁)
和朱令、孫維兩個典型的北京家庭壹樣,王琪和金亞的家庭也帶着那個時代的濃厚印記。王琪的父母是在陝西寶雞支援國家叁線建設的工人,金亞則來自新疆建設兵團所在的壹個小鎮。
青少年時代的王琪在鄰居眼裏是壹個活潑、聰明、有禮貌的女孩,走路連跑帶顛,遇到叔叔阿姨會主動問好,且記憶力超強,成績出衆,人稱“小電腦”。
“別的孩子學習時,抱着課本死記硬背,王琪從來不這樣,家裏書本扔得到處都是,她隨便撿起哪本就看哪本。”劉寬民是在王琪剛考上大學時搬來和她家成爲鄰居的,他在接受採訪時回憶道。
在王琪就讀的小學,記者遇到了她曾經的體育老師——如今是學校的門衛。他對王琪最深的壹個印象是“像個男孩”,這壹點和劉寬民的感覺壹緻。他看到過留着短發、戴着眼鏡的王琪壹邊吮着冰激淩壹邊蹦蹦跳跳地下樓,還看到過她穿着壹雙漏出腳趾頭的破襪子度過了整個暑假。
現年73歲的徐雲利是王琪家當年所在單元的組長,聽到“王琪”的名字時,她很快便想起了王琪父親的名字。在她和另外幾位老人的勾勒下,王琪壹家人的情況開始浮於眼前:
父親來自山東,母親來自河南,兩人在支援寶雞有色金屬加工廠建設時認識併結婚,婚後育有二女,王琪和她姐姐;姐姐壹樣學習很好,性格偏靜,後來考上了西安的壹所大學;幾年前,王琪的父母搬到了西安她姐姐家,爲她照顧小孩。
另外,壹位王琪中學的老師說,高考前王琪本已保送清華大學,但她放棄保送資格,執意參加高考,最終考取。
這個宿舍的4名女生中,金亞的經曆最不爲人所知。她來自新疆昌吉。1992年,從新疆昌吉直達北京隻有壹趟T70次旅客列車開通。直到2012年爲止,這還是唯壹壹列從新疆直通北京的列車。
與宿舍裏其他兩位舍友相比,朱令與同爲北京人的孫維走得更近。兩人加入了同壹個社團——民樂隊。
民樂隊裏壹位骨幹李偉對高個兒女孩朱令印象深刻——在這之前,清華大學民樂隊曾組織過壹場冬令營,當時還在上高中的朱令也報名參加,她填寫的特長是古琴。
“當時學古琴的少,我們對她很有興趣。”李偉說,“但是那壹次因爲朱令高中老師說朱令水平不行,朱令自己賭氣放棄了機會。”這壹次,朱令如願以償。上大學之後,朱令主動找到了清華民樂隊,表示希望加入。
因爲積澱深厚、琴藝出色,她很快被批準加入,併迅速成爲樂團骨幹。1990年代初,清華裏有民樂基礎的人併不多,很早就學習古琴的朱令因爲基礎深厚脫穎而出,除了擔任古琴獨奏,還擔任其他演出的樂器伴奏。
《老虎磨牙》是清華民樂隊的傳統曲目,進入民樂隊後,朱令從上壹屆學長們手中獲得了這壹合奏曲目中的壹個角色——負責小鑔,這是壹種流行於西南少數民族的互擊體鳴樂器。
除了古琴和小鑔,民樂隊還派給了朱令新任務——學中阮。朱令更願意把時間投入到古琴學習上,而不是簡單易學的中阮。但跟以往她做的事情壹定要做好那樣,兩年後,在民樂隊在“壹二·九”專場演出中,朱令已經成爲民樂隊的中阮首席。
除了別人的琵琶獨奏、二胡獨奏她不參加外,隻要有樂隊在伴奏,她都在場。
大二時,朱令參加了民樂隊在清華西階教室的演出。演出結束後,大家都在收拾樂器,這時孫維站在朱令旁邊,朱令跟大家說,這是自己的寢室同學,她很喜歡民樂,非常想參加樂隊。
此前,孫維參加過壹次民樂隊考試,沒能通過。李偉爲孫維又安排了壹場考試,這壹次孫維通過了。
據李偉回憶,孫維第二次考試成績壹般,但大家覺得她既然對民樂如此喜愛,“就讓她加入好了,專業技術可以通過努力來提高”。
因爲沒有民樂基礎,孫維的民樂隊生活是從學習中阮開始的。
中阮是壹種伴奏樂器,音色柔和,獨奏曲比較少,但門檻較低,適合初學者。這對同寢室好友在大二期間時不時壹起參加表演,在民樂隊另壹位表演者陳琳印象裏,當時清華民樂隊規模不算小,光中阮的表演者就可以坐兩叁排。
但跟朱令不同,孫維在裏面的表現併不出衆,陳琳對孫維有印象,是因爲民樂隊的樂器都屬於學校,壹屆壹屆往下傳,自己用過的中阮上有孫維的名字,她才依稀記得這個人。
壹位民樂隊骨幹說,孫維喜歡參加樂隊的各種文藝活動和Party,在樂器練習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多。
在母親朱明新眼中,這對室友在民樂隊的相處併不快樂。那段時間,朱令曾經問母親朱明新:“爲什麽壹個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別親的地步也總有不好的地方呢?”
“朱令開始慢慢覺得孫維沒把她當好朋友,老是使絆子。”朱明新說,朱令在民樂隊的活動本來就多,很少參加班級的活動,這讓她心裏很有壓力。
據她描述,有壹次,民樂隊的活動臨時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莊上古琴課,練完後回學校上自習,但孫維告訴班上同學說,當天樂隊沒活動。
“這樣壹來,同學更會認爲‘就是樂隊沒活動,朱令也不願意參加班裏的活動’,這件事讓朱令感覺很別扭。”朱明新這樣認爲。
朱明新還描述說,另外壹次,樂隊請了壹位老師來教中阮彈奏,孫維說朱令有基礎,不用學了,把朱令擠到了後面壹排。
但這些細節都未能得到孫維的證實。
11年後,2005年12月30日晚上,孫維在她的第壹次聲明中,將自己的性格解釋爲“直爽、心直口快且嘴有點‘損’”。
她拒絕承認自己小肚雞腸和好嫉妒,認爲宿舍的氣氛併不像媒體形容的那樣冷漠,“5年來,我們幾個舍友從沒紅過臉,至今仍是好朋友。”
而當時朱令也併未在意,隻是對母親朱明新說“孫維有點兒不懂事”。
1994年下半年,大叁上半學期,孫維“因爲功課緊張”退出了民樂隊。
“孫維走,我壹點印象都沒有。”李偉併不記得孫維是什麽時候離開民樂隊的,“如果是骨幹離開的話,我會知道,而且可能還要做些挽留工作”。
在這位民樂隊負責人的印象裏,在民樂隊,這對室友似乎併沒有表現出特別的親密。
多數時間,朱令對民樂隊的記憶仍然是明亮和歡樂的。朱令曾經多次跟母親提起自己對民樂隊的感情,“每天在食堂吃飯,碰到民樂隊隊員就擠在壹起吃”。
朱令的愛情也收獲於在民樂隊期間,她的男友是比她大3歲的學長,《老虎磨牙》這出節目裏的“老老虎”。
1990年代,位於西大操場西南的音樂室是清華民樂隊的活動地點。每個晚上,音樂室裏都會傳來琴聲。
那是朱令和她的民樂隊的同學們在練習——很長壹段時間裏,他們每週都會聚集到這間教室裏排練。
草坪上還活躍着另外壹支音樂力量,日後風靡校園的水木年華主唱李健是清華校園流行音樂派的代表,這是與民樂隊完全不同的壹支力量,他們逃課,用歌聲挑逗女孩,彈吉他,唱老狼、高曉鬆們帶點頹廢的歌。
朱令所在的民樂隊則代表着傳統,她時不時要參加壹些意義重大的演出。
1994年底,爲紀念“壹二·九”運動,民樂隊計劃在北京音樂廳舉辦以“韻我華夏,愛我中華”爲主題的專場音樂會,還邀請了很多校領導和民樂界的前輩參加。當晚,朱令將彈奏古琴獨奏《廣陵散》。
《廣陵散》是朱令最拿手的曲子,也是她在公開場合最後壹次演奏的曲目。這首關於刺殺的悲劇樂曲又被叫做《廣陵止息》,帶點悲怆地意味着人生落幕。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歲生日。爲趕“壹二·九”的演出排練,她打算與父親儘快吃完晚飯便趕回樂團,卻因爲肚子疼得太厲害,什麽也吃不下。沒過幾天,她開始掉頭發。到12月11日正式演出那天,朱令已經腹疼難忍。
演出結束後,民樂隊的成員在清華南門的壹家小餐館慶祝,大家哼唱着剛剛演出的曲調,所有人都很興奮。但他們事後回憶,發現朱令沒能參加。
“之後才聽說朱令當時已經3天沒吃飯,完全靠意志完成的演奏。”清華大學民樂隊壹位老隊員回憶。
演出結束的第二天,朱令回家,她告訴母親朱明新已經“疼得受不了”。壹個月後,朱令的頭發徹底掉光。在同仁醫院住了壹個月的院後,疼痛仍在加劇,但醫院卻始終沒有查出任何問題。
因爲擔心考試和功課,朱令不願在醫院浪費時間,隨即回到了清華。
環境係女生張博,曾經和朱令壹同上過“視聽練耳”課,曾意外地看到朱令“剃了個光頭,戴着頂帽子”,心裏嘀咕着:“真是特別酷!同班的物理化學課代表陳忠週回憶說:“那時很多同學都覺得她臉色有點蒼白,但沒想到已經病得那麽嚴重。”
女兒越來越弱的身體讓朱明新很不放心:“我每天下了班就到學校去給她送中藥、送面包,看壹下她情況怎麽樣。”看到朱令時,女兒已經連從床上下來、到床底下拉出紙箱子都很吃力了。
去照顧朱令時,朱明新和寢室裏的孫維有過壹次照面,孫維勸告朱明新:病來如山倒,勸朱令多回家休息。
這給朱明新留下了不錯的印象。“我對朱令說妳說人家不懂事,我看已經懂事多了。”
“壹二·九”音樂會結束以後,朱令已經大叁,她打算退出民樂隊,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和同寢室的姐妹們後來的選擇壹樣,那時的朱令也有着壹大堆計劃,她想選修計算機和其他課程,她甚至還計劃着選修清華的雙學位,併攻讀研究生。
復學壹個禮拜後,朱令的病情有好轉,走路時疼痛也稍許緩解,雖然朱令回家還帶着實驗報告,但其實她連寫實驗報告的力氣都沒有了。
那年寒假陳琳和朱令在清華校園裏匆匆見了壹面。那是開學前的某壹天,朱令穿了壹件大的羽絨服,戴了壹頂帽子——可能因爲頭發都掉光了。陳琳迎面打招呼,問身體好點了嗎?朱令回答“好多了”。這是她最後壹次見到朱令。
大約叁個月後,朱令第二次出現中毒症狀。此後,朱令的病情迅速惡化,由於呼吸不暢,在3月22日那天接受了氣管切開手術。
朱明新把自己的朋友請到家裏來,給朱令做全身按摩、用盆水泡,但都無濟於事。協和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李舜偉曾懷疑是“铊中毒”,但當時協和醫院沒有條件做進壹步的化驗。
朱令的獲救最終得益於當時興起的互聯網,在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網絡診斷,當年的媒體報道卻稱之爲神奇,《南方週末》在報道此事時用的標題是《神奇的網上救助》。
1995年,電腦、網絡對於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甚至連Internet壹詞也沒有確定的翻譯,直到後來才定譯爲因特網,國內隻有北大、清華和中科院聯了網。
朱令中學同學貝志城和他的同學蔡全清利用北大力學係機房的電腦連入Internet,爲朱令發出求救信。在隨後的十多天裏,貝志城等人共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封Email。
大量的英文信湧來讓貝志城等人措手不及,他和他的同學在北大發動二叁十名同學義務翻譯郵件。
日後,幾位朱令的接近者之間的矛盾也因網上會診而生。
孫維曾提到,1995年4月底北大的壹名同學來到114宿舍告訴她們朱令可能爲铊中毒,他們收到太多的電郵回信,希望可以幫忙翻譯。
孫維和另外兩名同班同學馬上去報告了係領導,併和其他幾位女生連夜翻譯。
然而,“連夜翻譯”的說法被貝志城駁斥:
“請問妳們何時翻譯過?我和我的同學壹個字也沒看見。最後,我的同學再次去時,壹位男同學勉強收下了部分郵件打印稿。”
貝志城的北大同學曾找到物化2班的團支書薛剛,希望他發動班裏同學幫助翻譯,貝志城稱:此後,他每次催要,都得不到任何翻譯的結果。
薛剛解釋說:他們併沒有打印稿,而是自己去北大取回存有電郵的磁盤,使用實驗室的電腦打印後,由包括孫維在內的班裏同學連夜翻譯。第二天,所有的翻譯和分析結果全數由係領導轉交協和醫院,係領導是物化2班與協和醫院所有聯係的中間渠道。
4月28日,再也等不及協和醫院做出回應的朱令家屬,拿着互聯網傳回的援助信息,將自己收集的朱令的皮膚、指甲以及血、尿、腦脊髓液等樣品,壹起送往北京職業病防治所,終於確診是铊中毒。
但爲時已晚。此前充滿朝氣的朱令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壹個瘦弱的、渾身插滿管子、陷入深度昏迷的朱令。
1997年6月30日,清華大學92級畢業典禮,天下起小雨,物化係的31人中,共有28人在那壹天領到了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
在這張不完整的名單中,除了因病休學的張利外,另外兩名缺席者分別是114寢室的朱令和孫維。
身中铊毒的朱令已經無法畢業,而孫維在畢業前夕被確定爲向朱令投毒的犯罪嫌疑人,4月2日被北京市公安14處以“了解情況”爲由從實驗室帶走,訊問了8小時。此後,清華以被公安調查爲由,拒絕發放孫維的畢業證書。
畢業典禮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辦了壹場盛大的音樂演出。壹位當天參加那場晚會的學生在水木清華BBS上留下了這樣壹段記述:
“到了正式演出那晚,大禮堂前草坪上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坐在草坪上,演出以大禮堂爲背景,中央台直播。因爲是慶祝香港回歸,所選的歌曲大多是激揚奮進的。
我記得有劉德華的《中國人》,羅大佑的《東方之珠》,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毛寧、楊紅瑩的《365天》,屠洪剛的《霸王別姬》,群星的《1997永恆的愛》。”
當晚演出,這片朱令、孫維、陳琳、李健都曾演出過的草坪被踩壞了。
由於身體原因正躺在醫院裏的張利沒有參加這場晚會,他說當時自己正處於人生最低谷,不想見人。
畢業典禮那天的小雨澆着這些年輕人,5年同窗後,他們即將踏上各自全新的人生旅程。
1992級物化班是物化專業最後壹屆5年製本科生班。當時出國很時髦,92物化的大多數同學都出國了。
“隻要是出國的,基本就沒打算回來。”張利說,當年球場上踢前鋒的女孩金亞在清華讀完博士後也去了日本。
(四)
畢業後,寢室姐妹王琪和同班同學潘峰舉行了婚禮,併共同進入基金行業。
多年後,潘峰在基金界壹戰成名,成爲清華物化係進入金融界的典範被師弟師妹膜拜。潘峰常叫上張利壹起去探望朱令。
張利說,大學時期的帥小夥兒潘峰現在憔悴了,有點駝背,頭發也少了。
2003年,張利也離開了清華,用他自己的話說,“幹起了個體戶”。
他最後壹次見王琪是2002年,最後壹次見金亞是她在清華讀博時,最後壹次見孫維則是在更早的1998年。
之後,關於她們的現狀再也沒聽誰說起過。
到了今天,很多人收獲了成功的事業、美滿的家庭,但他們中曾經的壹員——114寢室的朱令卻與這些永遠無緣。
因铊中毒損傷的不可逆轉性,即便多年以後,朱令的智力、視覺、機體和語言功能都沒有得到恢復,留下永久的嚴重後遺症,目前,朱令的生活仍然無法自理,智力隻相當於7歲的兒童。
對這個曾經優秀的北京女孩來說,她的人生被定格在1995年。
而對114宿舍的另外3位女生來說,這也成爲她們此後再也未能擺脫的陰影。
畢業後的孫維正如缺席當年的畢業典禮壹樣,也缺席了這個班級裏本就少有的幾次小聚會。沒有人公開提起她1997年後的生活。
關於她畢業後的經曆,網上流傳了多個版本。有人說她1997年因被列爲朱令案件嫌疑人,所以出國未果,後與壹名海歸結婚。
也有人說她嫁給了壹個美國人,已經出國,併獲得綠卡。
還有人聲稱她在2003年前後就職於諾基亞中國有限公司,後辭職離開。
但這些都隻是坊間的傳聞。這些年,孫維消失了。
2005年11月30日,壹則題爲《天妒紅顔:10年前的清華女生被毒事件》的帖子在天涯社區引起反響,帖子描述了朱令中毒的舊事,併直指孫維是投毒者。
多年前的事件再次激起波瀾,朱令和孫維的名字也重新回到輿論焦點。
那壹年,時值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又壹個春天。百度在納斯達克上市,微軟MSN、谷歌登陸中國,土豆、豆瓣、趕集等Web2.0網站開始嶄露頭角。
在那個沒有微博、微信的年代,BBS是公共討論的最主要平台。每天同時在線人數超過數十萬人的天涯社區,成爲最具影響的公共空間之壹。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數據,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國網民首次突破1億,寬帶用戶數也首次超過網民用戶的壹半。
網民數量的激增及網絡形態的不斷升級,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媒體生態,芙蓉姐姐、流氓燕、天仙妹妹等最早的壹批網絡紅人應時而生。
這壹次,在面對互聯網上衆多質疑時,孫維決定爲自己辯護。
她在天涯社區的天涯雜談版塊以ID“孫維聲明”發表了壹份聲明。
聲明中,她表示自己曾在1997年到1998年前後多次要求公安對自己進行測謊,均因各種原因未能如願。
孫維聲明發表後,有幾位物化2班的同學迅速用真名或化名在回帖中發言支持孫維,有網友發現,“最快的千字帖子在孫維發表聲明後4分鍾之內貼出”。
“她絕不是大部分人印象或想象中的‘高幹’子弟。”壹位名叫“太陽正暖”的網友說,這個ID自稱是孫維的清華大學同學。
物化2班原團支書薛剛也中途參與了進來,亮明自己的身份後,他對孫維及整個班級成員表達了自己的信任:
“至於我們的班級,我還是可以堅定地說,我們至今還是引以爲榮……我們堅定地在壹起支持孫維的勇氣,支持讓能思考的人們能更多了解方方面面的事實……
爲什麽僅僅抱住個別的言論,而完全忽略這裏這麽多同樣是朱令和孫維同學的聲音呢?”
在這次天涯的熱議中,孫維大四、大五的物化2班團支書潘峰2004年在同學錄的聊天記錄也被網友找了出來:
“就我所知,我們已向公安提供了所有已知的線索以幫助破案,到目前爲止併無結果,因此在查明真相的問題上,採用沉默是無奈的選擇。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隻能依賴公安,而不是衆多的網絡偵探和推理家;何況網絡上很多時候不怎麽講道理的,消息真假難辨,紛繁復雜,我們也根本應付不過來。”
多年以後,他在回復筆者的短信中確認,這確實是他本人的發言和觀點。
事後證實,這是清華物化2班部分同學壹次約好的集體回應,但後來有更多的同學參與了進來。
揭秘者是壹名黑客,他破解了孫維的信箱,然後將其發給了朱令的中學同學貝志城。
據被曝光的郵件顯示,孫維2005年12月18日開始計劃到天涯發帖,她告訴幾位要好的同學:
“我這些天很不好。我很難再保持沉默,我在考慮澄清。我現在把我所有的閑暇時間都用來起草這個澄清了。在發布前,我想發給妳們看看,妳們到時有時間看嗎?”
之後,她給幾位同學分配好了回帖內容及注意事項,如“多ID,多IP”、“千萬不要被記者的花言巧語迷惑”等。
在這些被黑客破譯掉關於“孫維和同學間探討聲明如何表述”、“同學如何加入跟帖”的電子郵件中能夠感受到,她們之間併沒有因爲朱令事件而疏遠,仍保持着大學同學的友誼。
孫維和大學同學在網絡上的表現,被貝志城形容爲“強烈的集體主義”。
他說:“這是壹個重視集體榮譽超過壹切甚至同學生命的班集體。”
2006年1月13日孫維發布第二份聲明,孫維對第壹個聲明中自己誤將音樂盒當成竊聽器的錯誤表示道歉,提到自己已經向公安提出了重新偵查的請求。
這條聲明發出後,在洶湧的質疑和猜測中,孫維再次選擇沉默。
朱明新稱曾接到孫維的母親來電:“她當時就是想要我們幫她澄清。但通過孫維的聲明,我們認定就是她(投毒),不會理會這樣的要求。”
2006年,物化2班同學童宇峰發起壹次公開信聯名,“請求公安重新偵查該案”。
張利負責收集簽名,他對筆者說:“2006年5月,收集到海外同學7份簽名,國內同學6份簽名。”
在他印象中,國內的女生,包括王琪等都沒有在公開信上簽名。
童宇峰在媒體上透露,征集簽名時,金亞、薛剛、潘峰等人都曾在校友網上要求修改公開信中提到的各種細節。
公開信的聯署和發布因此推後,而高菲、金亞、薛剛等人最終也沒有參與簽名。這封公開信始終未能面世。
2006年,張利用網名“百合之春”參與了在天涯上關於朱令案的討論,這場迄今爲止最熱烈的朱令案討論終結在2006年1月19日。
在天涯管理員發布了《暫停“朱令铊中毒事件”討論的通知》後,相關討論開始受限。
當時天涯的兩名負責人對媒體回憶,暫停討論是因爲接到了有關方面的通知。
據討論中的相互印證,以及張利的回憶,共有31人的物化2班,至少有包括孫維在內的12人參與了這次天涯討論,“王琪、薛剛、金亞都參與了”。
此時,記憶中的大學時光已經不再美好,因陰謀、構陷、謀殺等種種未經證實的指責蒙塵。
這壹年,當朱令案的討論在天涯網上分外喧囂之時,孫維和家人答應了鳳凰衛視“魯豫有約”欄目的邀約。
鳳凰衛視的工作人員近日在接受《叁聯生活週刊》採訪時稱,當年他們通過“孫維聲明”的ID聯係上了孫維哥哥。
在壹家咖啡館裏,孫維的哥哥訴說了家庭受到的困擾:幾乎無法繼續生活,即便搬家、換電話仍然不斷被騷擾,半夜被打電話、家裏半夜被塞進信。
經過幾次前期接觸後,孫維在人民大學附近的“魯豫有約”辦公室和節目組見了壹面。
據在場的人員回憶,孫維給他們的第壹印象是“瘦小”,跟網絡上貼出的微胖照片很不壹樣,“她身穿灰白色上衣,深色褲子,沒有化妝,跟着哥哥進來,感覺非常瘦小。以至我懷疑網絡上她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這次見面持續了3個小時,孫維再次強調了她以及家庭受到的騷擾和冤屈。
“她氣場很強。講述時語速很快,也很平靜。我記得她說,很多人打電話去她爸爸的辦公室,以至於她爸爸爲了躲避鈴聲躲到椅子下面。
她自己也有幾次試圖自殺。有壹次因公出差到了壹個海邊,她就想跳海死了。她很詳細地描述了海灘的氛圍,她如何在海邊徘徊。”壹位鳳凰工作人員接受採訪時說。
但這期節目最終併沒有錄製。2006年,在接受《青年週末》採訪時,《魯豫有約》執行製片人曹志雄透露,孫維不接受採訪是擔心這種情況下出來說話會與網上形成壹種因果關係:“妳逼我,我就出來說話,那妳逼我不就有成效了嗎?”
而與之相伴隨的,是網上幾乎壹邊倒的輿論壓力,這甚至波及到了鳳凰衛視的工作人員。
在孫維要上“魯豫有約”的消息傳出去之後,他們中有人收到大量電郵、電話、短信,持續不斷,言之鑿鑿地稱孫維就是兇手,“妳會感到壹種很強的訴求撲面而來。這股力量是很嚇人的”。
節目的夭折,從側面印證了朱令案的復雜與糾結。壹方面是民意洶洶,壹方面是取證機構保持沉默,案情由此更顯得雲霧重重。
7年後的2013年,壹起發生在復旦大學的投毒案又將朱令案帶回公衆視野,壹家中央媒體的記者邀請孫維接受採訪,後與孫維母親見了壹面。
孫維的壹位家人談及這位記者和孫維母親見面情況時說:“孫維還是頗有顧慮,她不喜歡媒體先入爲主地把她當成嫌疑人來問話。”
孫維在2005年的聲明中提及,1998年8月26日公安宣布解除對她的嫌疑,在市公安14處領導和主要辦案人員都在場的情況下,她再次提出要求進行測謊,被立即拒絕,說“沒有必要了”。
在孫維的聲明中,她提及自己甚至花了很長壹段時間搜集和研究關於測謊儀的知識,她認爲,測謊儀雖然準確度上有風險,但在案件沒有偵破情況下測謊是能還她清白的最好辦法。
“我實在不願意不清不白地生活,因此儘公安從未提出過,但我仍然主動要求對我進行測謊,卻未被接受。”孫維在聲明中這樣說。
當2013年4月,復旦投毒案又壹次將朱令案激活的時候,微博已經取代了8年前的BBS,成爲最重要的公共討論平台。
但這壹次,孫維和她的同學們沒有出現在戰場上。雖然他們當年在天涯社區上使用過的老ID還在發言,但此時已無法證實這些ID的使用者是否他們本人。
這壹次,網友宣稱孫維改動過身份證信息,她的哥哥以及丈夫微博信息也相繼遭到曝光,丈夫謝飛宇是她高中時的同班同學,本科同樣就讀於清華大學。
4月18日,“孫維聲明”的ID在天涯發布了帖子《這麽多年,和很多人壹樣,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壹天》。
這壹次,帖子裏隻有簡單的壹行字:“去去醉吟高臥,獨唱何須和。笑罵由人。”
在此後壹個多月時間裏,這個ID不時回帖跟網友交流,時而表現得嚴肅認真,稱自己“恨事情沒有發生在今天,埋沒了真相”,“比任何人都想將真兇繩之以法”;時而語氣調侃幽默,使用壹些熱門網絡語言,併自稱“铊姐”。
但這個ID的使用者是否依然是孫維或其家人,目前無法確定。
在5月8日回復筆者的私信中,孫維的哥哥稱:
“孫維有關此案的所有答復請參看天涯論壇2005年12月30日的聲明及隨後關於‘竊聽器’的道歉,我們對聲明及道歉兩文中的文字負全部法律責任。”
他併未提及這個ID發表的其他言論的真實性。
當年114寢室的姐妹之壹王琪和丈夫潘峰,也正在遭遇暴風雨般的網絡搜索,網民針對他們所在基金公司發起了“隨手撥”行動壹壹
即不斷打電話給他們的基金公司,讓其電話銷售徹底癱瘓,壹些網民甚至呼籲做空這對夫婦所在的基金公司。
此前在日本做客座研究員的金亞如今已徹底消失在公衆視野中。
有人在2011年看到她出現在日本愛媛大學,網友質疑金亞是幫兇抑或兇手的郵件,擠滿了她的導師和該學校另壹位教授的郵箱。她的導師拒絕了採訪請求。
2007年,“幫助朱令”基金會的何清到日本見過金亞。他到學校實驗室正好碰見壹個小個子女孩,剛好就是金亞。
何清在接受《叁聯生活週刊》採訪時回憶,金亞對她的來訪併不是很樂意,但還是壹起去附近的咖啡館聊了壹會。
談話是在何清保證“客觀”,併表示不會將談話內容發表到網絡上後進行的。
“金亞說,這個案子非常復雜,牽扯到很多人,公安都沒有結論,我們怎麽知道誰是兇手呢?
我對金亞說,這件案子對我們來說很簡單,併不復雜。金亞說,那是妳隻看到壹個分支,但這件事情有很多條分支。她用手指在桌上畫了棵樹的形狀。”
“最後金亞說,公安有我們所有的問題記錄,我們在每頁上都有簽名。當有人再來問我這案件時,我告訴他們,去跟公安談。如果公安要重審這個案件,我很樂意自己買機票飛回北京協助調查。”
這麽多年過去,物化2班從沒有舉行過集體聚會,隻是還在北京的男生會偶爾組織壹場,在廣州工作的潘峰偶爾會趕來參加。
張利記得,聚會席間,大家有時會提起朱令,聊到她現在的身體情況。
在聚會時,大家曾試過幫朱令找醫生,當時考慮找中醫,後來覺得不靠譜,就放棄了。
“基本每次聊,都是壹帶而過,因爲多說無益,又能怎麽辦呢?”張利說。
另壹個生活被朱令案緊緊纏繞的是她曾經的男朋友。他至今工作在清華校園,這些年來,他拒絕了所有媒體的採訪。
在互聯網上,圍觀者強烈指責他棄朱令而去,在案情上也從不公開發聲。
但這種指責併不公允,據李偉和古琴老師介紹,在朱令中毒後很長壹段時間裏,他和朱令的家人壹直輪班照顧她。
李偉說“當時他們的關係也僅是朋友,從這壹點來看,我們覺得他已經做得很好了。”在結婚後,他和夫人壹直熱心於“幫助朱令”基金會事務。
114寢室4姐妹自從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聚到壹起,她們錯過了若幹次機會。在孫維第壹次聲明中,她說自己曾兩次提出跟朱令家人溝通,但都被公安拒絕。
朱明新併不認可孫維的說法,她說:“我壹直想和孫家溝通。”
畢業之後,王琪隻有壹次跟朱明新提及希望到北京看看這位生病的昔日室友,但這個希望併未實現,她的丈夫潘峰則是去朱令家次數最多的人。
王琪告訴記者,她正在向警方提出信息公開申請。
潘峰也說,這件事最缺的是透明,透明的最好辦法也是警方對當年辦案的信息公開。
對網絡上的指責,朱令的這些大學同學表示無奈。所有被網民懷疑跟朱令投毒者有關聯的人都被網絡搜索過千百次,他們的名字、身份證號、車牌、人生履曆都被人壹遍遍翻出來。
現在,潘峰仍堅持2005年自己所持的觀點,他對本刊記者說,故意散布謊言或不真實信息,這不能完全用“偏見”來概括,“用正義的名義做事,更具欺騙性”。顯然,這代表了他對網絡的態度。
朱令的家位於南叁環壹個1990年代的小區。
筆者到訪的當天,七八個記者正在採訪朱令的父親吳承之,他坐在沙發上,握着遙控器,面前的電視機正在不斷播放2007年央視“東方時空”紀錄片《朱令的12年》,這是央視壹個團隊曆經壹年多,拍攝的朱令中毒後到2007年間的生活情況。
影片比較重要的地方,吳承之就按暫停,對在場的記者講解。
節目中播出了清華女生朱令剛入校的樣子,在層疊的山巒的背景裏,朱令壹身深藍的夾克、壹條黑色的褲子,孫維則身着豔麗的橙色夾克和藍色褲子,照片中,兩位女生就像美麗的公主。
在這壹係列照片中,還有這樣壹張——孫維和朱令戴着墨鏡,朱令擡着孫維的壹條腿,另壹位同學托着孫維的壹隻手臂,兩人面帶笑容。
另壹張照片中,朱令牽着孫維的手,兩人眼睛朝下看,應該在探路。朱令摘下了墨鏡,露出帶着嬰肥的臉,嘴角上揚。
張利對同班兩位女孩的青春照片也記憶深刻,坐在地鐵站附近的茶館裏,他立刻回憶出她們的樣子:
“照片很土。”
“妳看,孫維身上的夾克明顯比她大壹號。”
“現實中,她們比照片上的更好看。”
……
在當年爲數不多的照片裏,她們常會像姐妹壹樣緊緊摟抱。
不知道孫維有沒有想到,這位至少和她拍過兩次合影的大學室友朱令,會和她此後的壹生緊密地纏繞到壹起。
現在,朱令已經失去了照片裏的青春面容和姣好的身材,她的體重達到100公斤。
因中毒全身癱瘓,隨之而來的是大腦萎縮、雙目近乎失明、基本語言能力喪失……生活全靠年邁的父母照顧。
照片上的另壹位女生孫維,壹度被作爲朱令中毒案中的嫌疑人審訊,儘管警方壹再宣布解除了對她的嫌疑,但她如今仍被搜索、诠釋和指責。
沒有人能在現實空間中找到她,5月24日晚上,“孫維聲明”這個ID再次發言,無從了解這個ID此刻的使用者是否孫維。
該ID以孫維的口吻表達了跟她的反對者同樣的擔心:“司法不獨立,重審,不過是用偽證證明我是兇手而已。”
張利已經多年沒有回清華看看了,如果他回去,也許會怅然若失,他們曾經生活的印迹已蕩然無存。
1992年朱令所在的宿舍6號樓,後來被推倒、拆毀,鐵皮圍着的高牆上頭,有壹棵樹冒出頭來,樹頂的枝葉全被砍去,隻剩光禿禿的樹幹和大枝桠。
附《朱令十二年》視頻: